阿乙
来到,离出门第一站郑州近了,我能看到往事跟着风一起吹过来,。在那个灰雾笼罩性情逼仄的城市里,我看到过光明,又看到光明沦陷——一个大老男人在情感的剧变后,终于明白,如果裘海正是俗的,那么就是俗的。裘唱过《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以后我每离开一个城市,都能幻听到这直爽得怕人的歌声。
昆德拉和阿兰·德波顿两不遗余力干的事,其实就是论证世界上永远没有投缘的男女,你永远找不到另一个“我”,你所理解到的别人,和别人本身是两回事:一个从卫生间出来满面红光的人成了你一瞬而永恒的女神,但那女神彼刻却明明是在焦急地手纸。而多场恋爱给我提供的丰富也就是“忘我”,我要喜欢一个人,我就忘记自己叫什么,我努力按照她的想法去看待问题,她今天长痘痘了,我便缓解她的心理压力,说老夫我“有心长痘,无力回天”。
我挺贱的,我把女人都当成了,不拍几下心里就不舒服。我就是在这件事上觉出“我们”两字实在是人生之大荒谬,“我们”躺在床上,“我”非常想睡,“另一个我”却在不停地吃零食、唠磕,间或还要制造点鼾声,逼得“我”自杀不成非要他杀。在《新世界》里,“我”只要喝点药,便能复制出“我”来,如此循环往复,“我们”两个字便得到完美的构成,没有任何一个“我”出来反对“我”,《》()。
而根据我理解,现实中参差不齐的人,之所以被统称为“我们”,也只是在某种情形下形成了卑劣的妥协。比如我想吃某人的食物,同时你也想吃,饥寒交迫的你我便在血泪控诉中形成了同盟关系,此所以“我们”。但只要永恒的利益一发挥作用,永恒的我们便又死翘翘了。我如果食物分少了,我是一定不干的,你再敢说“我们”,我就要控告你强奸。
说到强奸,这个世界凡有乌托邦,便会有这东西。在乌托邦的世界里,“我们”是出现得最多的词,“的”不是。某天下午,我在醒来的时候突然发现,其实每个独裁者都是心怀的,因为我发现自己也有独裁和统治别人的念头,而我是那么地这个世界——我只是不放心别人,我只是认为只有我才能办好这事,才能带领大家走向光明。这样,一个本来大而无当的“我们”便变成了“以我为主的人们”,我在前,你们在后。如果换成强奸的说法,便是我在上,你们在下。
扎米亚京写的一部乌托邦小说就叫〈我们〉,在彼世界里,人被编号,称作“号民”,跟我看到的养鸡场一样,17号小姐或者29号小姐,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奴役起来十分方便。而所有的乌托邦小说似乎都爱塑造一个超强的演说家和一堆弱智的号民,这个持有权力或夺取权利的演说家面对无限复制的羊羔,像一只狮子一样,负责而深怀大义。
我不喜欢鼓动性的语言,不喜欢鼓动性的人,不喜欢动辄就喊“我们”的人。每个人的荷尔蒙分泌状况都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你要是爱干“革命”,你就去,不要拿着阳具招摇过市,一定说要代表“球迷”。今天罢赛,是为球迷,明天不罢赛,也是为球迷——球迷跟卫生纸一样的。
我活在堕落的边缘已经很久,今天上网看到丽贝卡要出了,听说还要曝一些床上的秘闻,我喜欢。我最不喜欢读的作品便是自传,自传颇似一次意淫的公开宣扬,从来没有一个“干净”的人会在里边抖露自己嫖娼的旧事,从来都是自己像山一样出现在封面上,俯视一切,教育一切。我期待丽贝卡写自己,是她没有那么多的自由、女权主义要宣扬,她需要钱而已。
写完这个,我等着另一个极度虚无的人出来写:我死了。
〔最近的专栏(权做乌托邦小说读后感)〕随文赠言:【受惠的人,必须把那恩惠常藏心底,但是施恩的人则不可记住它。——西塞罗】






 猜你喜欢
猜你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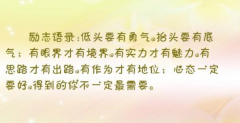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