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么?我分明看到了岩石凹进去的轮廓一如打坐的佛之剪影。那佛面对的前方一二百米处就是韦藏活佛的修行石窟。端起相机,摄下了我的发现我的奇遇。我将相机里佛像模样的图案指给年青的鲁布普仁列喇嘛看,他说,确实像,以前还真没人发现过。一行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庙后空旷干燥的山谷会有久久升腾的紫雾或是雾气?而我欲解未解的是遇到岩壁佛像剪影的机缘?”
作者张友文利用旅途间隙研读
上述文字出自蒙古族作家韩伟林散文集《画中故乡》(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6月版)中的《剪影》。从这段文字中嗅出了作者感知敏锐的程度和慧根的深浅。此段文字描述的现象同样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认为有些大自然奇观,凭借目前的科学水平不可解。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科技的进步,谜底早晚揭晓。如“为何庙后空旷干燥的山谷会有久久升腾的紫雾或是雾气”这个谜,凭常识断定,或许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关吧!可是,佛像模样的图案的确是一个不可轻易解释的现象。在我看来,这还是一个心理学难题。如果由我来看这一幅图景,断然看不出。为何伟林能看出呢?窃以为,这是“期待视野”(德国美学家姚斯语)使然。
文学作品是能带给读者审美愉悦的精神产品。无怪乎宋人苏轼说“诗以奇趣为宗”(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清人黄周星则认为好戏曲可用“趣”字来概括,即趣人、趣事、趣境、趣字(《制曲枝语》)。同为清人的史震林也认为:“诗文之道有四:理、事、情、景而已,理有理趣,事有事趣,情有情趣,景有景趣;趣者,生气与灵机也。”(《华阳散稿·序》,《弢园丛书》,清光绪九年铅印本)
在此,借用清人史震林之说,《剪影》中所记就算景趣了,毕竟这个“佛像模样的图案”留给我们读者无穷的遐想。再细读,我们会发现这么短的一段文本中就有两处略带神秘意味的景趣,这怎能不引发作者和读者的想象?
下面还是围绕“趣”字展开,接下来则属“事趣”范畴。恕我直言,我并没有细读《画中故乡》中的每一篇,大约只读了三分之二。但是,过目的文字中有三件趣事让我刻骨铭心:一件隐藏在《二连》中,如“我还读到这样的离奇故事,我方边检人员与蒙方边检会晤,强行给对方读毛主席语录,使对方处在被动位置,认为是胜利。一次,就中方一条黑狗在驱赶蒙方越境马匹时被蒙方哨兵开枪打死一事举行会谈,蒙方听完事由后表示‘此事不值得会谈’。我方小题大做,态度严肃予以反驳。有的官兵甚至提出,与修正主义没有什么互谅互让,只有斗争,方不失为大国的体面。从1966年到1976年,中蒙双方边防检查站举行的业务会谈会晤,仅有6次。”如果伟林不深入采访,不费一定的脚功,我们读者也就不会知晓这一段让人莞尔一笑的“历史”了。事实上,此作既可划归反思“文革”的篇什,也可归入“理趣”之列,毕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国别的读者从中读出的感受肯定会大不一样。而在《曾经那些流变的边界》之中,“1881年的《中俄伊犁条约》和以后的几个勘界议定书,清朝西北霍尔果斯河以西的7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并入沙俄版图,运行了125年之久的清代乌里雅苏台卡伦道路结束了它的生命,因为中俄划分的新边界,以乌里雅苏台冬季内卡伦道路,即以中国国内交通线作了两国国界”。他人眼中无足轻重的一角资料,伟林读到了并且平静地撷取,因为他眼中的“事趣”隐藏有家国的深痛。
事趣能引发读者的好奇心,紧扣读者的心弦。如果说上述趣事是特殊时代的产物,那么另一则趣事则是个人原因引发的。且看《真情像草原一样宽广》中有这么一段:“新巴尔虎右旗克尔伦边防派出所教导员陈淼,不说成绩,谈的是自己的‘丑事’。那是1997年7月的一个晚上,一名到派出所报案的蒙古族妇女情绪激动,陈淼费劲了解了‘情况’,一男子酒后经常骚扰并殴打她。陈淼不问青红皂白询问该男子:以后不准再到她家,打她,否则拘留你。男子见状,仓皇而逃,可事情并没完,几个星期后,那名男子放牧不小心越入蒙境,被遣返回国。‘警察不让我回家!’男子所说的话很快传到了陈淼耳中。人家是夫妻,妇女来报案是因为男子醉酒后打了她!知道真相的陈淼羞愧万分,开始发奋学习蒙古语,成了名符其实的“蒙语通”。从这则趣事中,我倒是看到了边防派出所教导员陈淼勇于担当与自省的责任意识。如果跳出文本,“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换言之,用社会历史批评来解读,从这则趣事也可洞见伟林严于解剖自己,十分难得,十分可贵,大概要算此集的精魂。
情趣在《狼烟·卡伦》中已显露出来。当目光移至此文本时,不需我自己去发现或提炼其“趣”,体贴的伟林早已替我找到了,如“古人也很有趣。边防小城的生活总是寂寞,那就忙中偷闲吆五喝六小酌相聚。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出土过一批文物,其中就有一张元代距今700多年的请柬。请柬写得简短、精彩:“谨请贤良/制造诸般品味/簿海馒头饰妆/请君来日试尝/伏望仁兄早降今月初六至初八日/小可人马二”。品着这则充满雅趣的请柬,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唐代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元代的请柬和唐代的诗歌相较,虽说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文本,但是它们所书写的内容(事件)是相同的,所传递的情感也是相同的,凸显的都是真挚的友情,表达的都是人类相通的情感,正如阿·托尔斯泰所言:“艺术就是从感情上去认识世界,就是通过作用于感情的形象来思维。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形象应该对感情发生作用。”(阿·托尔斯泰:《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而在《沉静如初》,伟林看边境线上的岩画,那是远去的智者“或向祖先传达一种信号,又或和族人进行一场较量,争夺狩猎场,争夺美丽的姑娘,或者只是留下一段心事?……那画里,有了他们的眼神,有了他们的爱意,至于他们用了什么语言,听说,留存在了那一幅幅画面的四周。不经意间,天地变得湿润”。再来发掘伟林散文集中所蕴含的理趣,只要稍稍用心,就能撷取一二。如《满洲里的国门》中有这么一句:“当沙俄修筑的旨在吸取中国资源财富的中东铁路轰隆隆地运走大量物资时,客观上也在帮助中国运送了救国救民的精神财富”。诚然,这充满悖论的言语中,却包孕辩证的哲理,自然会引发读者对某些社会问题的思考。
因篇幅所限,不可能篇篇俱到、句句论及。《画中故乡》中的景趣、事趣、情趣、理趣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互为依存,互为补充的。
要言之,该文集让我刻骨铭心的当属富含“奇趣”的文字,无怪乎明朝李贽夸张地把“趣”当作天下文章的第一要求,说文章有趣才有看头。
走笔至此,本可以停止敲打键盘,但还有一点不可不说,那就是从宏观角度观此书,其价值是丰沛的。上面所述仅仅是其文学价值的冰山一角,而地理学价值、史学价值及民俗学价值等也是一言难尽的。







 猜你喜欢
猜你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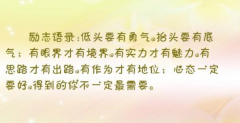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