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神逃逸、信仰缺失的现当代,有关宗教、神性的话语或主题并没有消减。以文学写作而论,神性写作在八九十年代一度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路向之一,在莫言、马原、扎西达娃等先锋小说中也弥漫着神性元素。然而在散文写作中,或许是因这种文体与世俗、日常的天然关联,神性的倾向或元素一直处于稀缺状态。最近读嘎玛丹增的散文集《神在远方喊我》,则改变了这一印象。作者以丰满而灵幻的文字,力图在现实、历史和宗教的三维缠绕中,迹写漫游、徘徊青藏高原时对于神性和人性的独特体悟与私人剖白;与此同时,通过灵与肉、生与死、人性与神性、汉文化与藏文化的擦击与碰撞,传达对现代文明和当下困境的忧思与揭蔽。这种写作,在作者那儿可以视作一种自省、渐悟、修行;在我看来,它已经具备了当代启示录的性质。
嘎玛丹增并非那种走马观花、喜好猎奇的旅行者,本集中的大多数散文既非通常所谓的游记,也非那种哲理散文。我以为,它更像是一次次回旋曲式的精神漫游,带给读者的感受如同一次精神洗礼和心灵历险。读这样的散文,扑面而来的是青藏高原的酥油气味和雪融般的灵魂气息。可以这样说,抵达心灵的神性光束,在他的字符里转化成一种天启般的悟性和忧思——他用那根在神境点燃的灵炬从内部照亮文字,为当下提供一面灵魂之镜,然后传递给他的读者。
在我看来,作者首先是带着个体的精神迷惘和对文明的质疑上路的,并在路上产生新的困惑与追问,诸如:“我们的心灵病了,这是一个事实”,“天堂这个名词,已经被人当作一种无力相信又无法抛弃的形容,并一再被滥用”,“信仰的缺席,就像很多真相和事实的毁灭一样,得到了时间和财富的默许”,等等。这种困惑和质疑,为探求与描叙青藏高原的雪山、寺庙、树林、民居、唐卡,向后拉开了一抹幽蓝的精神纵深。与此同时,对藏地生态环境的受损和工商文明的侵蚀所传达的焦虑,则向前辟出一片峻切的时代开阔地。而这,正是一般游记和哲理散文所匮乏的。
然而,作者从不摆出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姿态,而是拿自己的灵魂透视、剖析,裸露内心的卑琐与私密,足以见出一个写作者的坦荡与真诚。“我每次仰望佛像、菩萨和护法神像,好像被人脱光了外衣站在法庭,等待接受精神审判,难免惶恐。这种慌乱只在内心瞬间显现,别人难以从我的表情中觉察。我在长期的世俗活动中,学会了掩藏和虚饰,很少直面自己的心灵。”(《站在过去城堡的门口》)这种难得的自审、忏悔的精神,也是一般观光客所不具备的。
我还看到,作者在藏地的游历与追寻,日渐融浸于立体呈现的藏地的历史与文化,反过来又加深了对生存于斯的文化生态和精神状态的关注与关切。他移动在高原的脚似乎生出了根须,具有观光客或旅行者所不具备的“生长性”——他虽然不是出生在那儿的藏人,但他的“灵犀”是与藏人相通的,并因此交上了不少相契相印的藏族至交。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说他“皈依了‘嘎玛丹增’这个名字”——嘎玛和丹增这两个词,一旦组合便产生很深的宗教意义。因此,这次更名在他的精神旅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象征意味。在我看来,“嘎玛丹增”这名字,更像是他这棵移植之树开出的一朵格桑花。
众所周知,一般游记是写景不记人的,尤其不会以人为核心来写。集子中有不少篇什将“人”置于神性背景的前台,他要观察、探求的是藏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秘密。他与藏人打交道之广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诸如牧民、喇嘛、沙弥、匠人、朝圣者、奇人、向导、阿妈、康巴汉子,以及叫丹增、格敦伦珠、尼玛措的孩子们。例如,在《泽戈兄弟》、《海子山雪雾》、《佛在一切正确之上》和《高山仰止》中,作者多次写到一个叫泽戈的藏族汉子,那是在一次车祸中偶然结识的朋友。显然,与泽戈的深度交往不是一个游客,也不是一般汉人所能做到的——那是两种不同成长经历、不同文化心灵的碰撞、对话与交契,而无法融合的“冰点”一直潜存着。“多少年来,我和泽戈一次次重逢,又一次次告别。在聚聚散散的人生中,完成了我对一个兄弟、一个民族从陌生到接受、融合、崇敬的过程。信仰的缺席,决定了我不能深入泽戈的世界。不同的文化背景,把我们安排在不同的道路上颠沛。”与一个藏人朋友交往,不仅关涉对藏文化的了解,细微到对诸如酥油味道的接受,更关涉对精神信仰的体认与尊重。
与之相对照,他看清了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灵魂生态,并加以拷问与揭蔽:“我们的心灵病了,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物质帝国难以掩盖的真相。……各种灾难、杀戮、争斗、不明瘟疫和有毒食品,频频以推陈出新的奇怪面孔出现,让我们时时惊恐不安。我们的世界病了,并迅速殃及社会环境、自然生态、人文地理和精神价值体系。这种文明的疾患,最终导致人们对一切本真事物的不可信、怀疑,并坚决拒斥,把我们追寻真、善、美的人生理想彻底剥夺和颠覆。”
从文本写作角度说,作者避开了通常游记那种单线条的时空架构,多以精神凹镜透视藏地的一切,将描述、具象、隐喻和箴言复合一体,由境入镜,以镜证境,尤其将价值判断置于二元互否之间从而使叙述具有了复调性,表层的空间述它因此转化为深层的形上述它。在《毛垭大草原》中,作者抓住并颠覆了“新”与“旧”的主流观念,意味深长地写道:“一切都是旧的。只有路是新的,比大地上的一切都新。……‘要致富,先修路’,已经成为世界奔行在文明尾部的六字谶语,正在不计一切后果地改变和清扫道路前方,那些越来越窄的传统空间。……对文明的入侵和必然,我们应该满怀感激,还是应该谨慎抵抗?只有时间清楚。但很显然,如果没有这条道路,我确实走不到毛垭大草原,走不到这么旧的地方。”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夹叙夹议产生了思之张力,准确把握了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双向特征。又如在米玛家的“土掌房”里作客时,他再次描述了那种“旧”——原始、简单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方式,顺势与现代城市畸形之“新”加以对照。作者最后写道:“我们的汽车带着米玛和阿妈拉,奔向了朝觐的道路。也许,这就是一条古代的朝圣路,……只是那个时代还没有水泥道路。我们也不应该坐在汽车上。于坚说,‘汽车的速度,无法通向神灵。’”这种肯定和否定的颠覆与循环,呈述了人类所处的无奈的两难困境,比起单向的肯定或否定来得贴切、深刻。
与此相应,作者还擅长在虚与实、叙与议、此与彼、天界与尘界之间腾挪、闪跳或并置,将个人体悟和理性锋芒像砂粒一样嵌入其间。例如,作者抵达扎日沙巴神山后写道——






 猜你喜欢
猜你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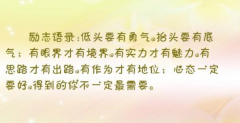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