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花两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平萍的长篇小说《盲点》(河南文艺出版社于2011年12月出版),发现其中令人“震颤”的场景实在太多。侦探小说鼻祖爱伦•坡认为,文学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达到“一种效果”,即作家通过艺术创造使得读者得到某种刺激,比如恐怖、震颤等。特别是那支肇事的“七七式”小手枪频繁惹事,致九死二伤,从而使文本充满奇幻色彩。那只小手枪作为意象自始至终都活动在文本之中,丰富了文学性的同时,又强化了“整一”性。
《引子》除外,故事从起笔到止笔跨度时间不过一二十年,但是,其中的爱恨纠葛却让人刻骨铭心,官场的潜规则被揭露得淋漓尽致,警界不为人知的一面也尽情展示。
丹麦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勃兰兑斯说:“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诚如是,《盲点》中人物心理刻画入木三分,各色人等的心理较量战栗而真实。譬如妖冶的留英法学博士、女公安局长助理郝嫣然和睿智的法学学士、女刑警支队长肖芃两人长达一二十年的明争暗斗竟然是为了一个男人,乍看初读会觉得不可思议,等到我们读者真正沉浸其间,走进她们各自丰富的内心世界,才知那是艺术的真实、情感的真实。这个男人系原刑警大队长平炜,他那美好温馨的家庭因郝嫣然的父亲而毁。美得令肖芃嫉妒的郝嫣然之所以爱平炜爱得死去活来,是因为他的英俊潇洒,还是因为他铁骨铮铮的人格,抑或是出于补偿的心理,谁能说得清?等到发现平炜并不爱她时,她竟伪造证人、证言等证据,将平炜送进监牢,自己却远走国外。郝嫣然阴鸷、忧郁,颇似蘩漪,堪称“这一个”。她那美丽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交织着最残酷的爱与最不忍的恨”的独特灵魂。曹禺在《雷雨·序》中意味深长地指出蘩漪的独特个性:“她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同理,郝嫣然这个人物的可爱在于她的不可爱之处。
肖芃这一警察倒是非常阳光,但又不能用“崇高”、“伟大”等宏大字眼来界定。她的几分真勇、率直、果敢、机智、重情讲义让这个人物呼之欲出、活灵活现。她对平炜的爱是真诚的,纯粹是出于爱慕与感佩,不含一点杂质,没有丁点功利色彩。她敢爱敢恨、嫉恶如仇、勇于担当,不愧是警界中的女杰。她为了给平炜平反昭雪,竟冒天下之大不韪越级向领导进谏,她的泼辣又让这个人物个性增添了几许色彩。如果整部小说一味地讴歌肖芃,没有道出她内心的渺小,这个人物就会显得不真实。聪慧的平萍通过制造幻觉来刻画这个人物的内心,如肖芃在擦拭“七七式”小手枪时,“她对着窗户外面的天空,神神叨叨地默念了什么,好似看见那片天空中幻化出来一个妖冶女人的脸庞,笑盈盈的。”这段心理描写是肖芃潜意识的流露。紧接着,“她扣动扳机……”由此可见,正直、刚强的肖芃也有置情敌于死地的阴暗心理,正如法·罗曼·曼兰《约翰·克利斯朵夫》扉页所记:“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如此运笔,便直抵肖芃的灵魂深处,将这个人物打造得较为成功。
郝嫣然虽算不上警界败类,但她那病态的灵魂、颠倒黑白的行径显然对公安事业的发展是有害的。那么,她又是如何混进入公安队伍的呢?一向看问题非常深刻的平萍直指官场的盲区。
《盲点》表面上是在说枪支管理方面的盲区,像“七七式”小手枪因疏于管理,才导致一系列让人心颤的悲剧。这些悲剧并不能制造悲壮之美,倒是引发胃痉挛。实质上,枪支不是活物,让枪支生事归根结底还是人。例如,当歹徒抢那支“七七式”小手枪时,王子乐副大队长本可以将他击毙,可是,在那紧要关头,却发现没有子弹,个中原因直到小说结尾才揭开谜底。如果说王子乐的死亡是因为郝嫣然有意把子弹取出所致,与权力沾不上边的话,那么,其他枪案的发生皆因权力惹祸。大队长要用枪,内勤不敢不给,结果导致大队长的两个儿子死亡。当时若有人稍稍制约大队长,惨案就不会发生。后来,由肖芃起草的枪支管理的规章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某些人手中的权力,可喜可贺,更令我们今后要警醒。
要言之,这篇小说隐喻意味颇浓,它借枪说事,旨在直陈官场盲区。它虽然没有直面官场,言外之意对吏治的腐败是深恶痛绝的,旨在直面警界非人性化所在,从而期冀警察尽快走出盲区。但愿此作的问世能促进当下民主法制的进程,对某些官员的胡作非为能起到了敲山震虎的效果。






 猜你喜欢
猜你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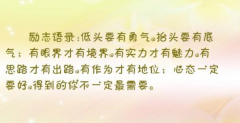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