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飞是一位左手小说,右手影视的两栖作家,我们在电视剧《旗袍》中,看到了他对旧上海及上海情感的描述。接下来他的中篇小说《捕风者》《麻雀》亦先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并被各类选刊迅速选载。海飞同样将两部小说的背景设定在上海的孤岛时期—— 一九四零年代,一个注定混乱不堪而精彩纷呈的年代,如此专一地选择同一个地域来生发故事,或许这是海飞对上海滩的情有独钟。
小说本该以虚构见长,但《麻雀》和《捕风者》给我的感觉像是观看画面已经泛黄的旧电影。海飞严谨地按照真实的细节,还原着逼真的旧上海,不仅包括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还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他甚至还写到了工部局屠宰场,如今这个曾经每天都能听到猪牛牲畜嚎叫的地主,早已成了一个休闲的餐饮咖啡吧聚集地。他的严谨最终带给我一幅旧上海的画卷,徐徐展开才发现一幕幕活剧正在精彩上演,分不清是虚构还是现实。
海飞很高明地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冷静的叙述者,不动声色地将孤岛时期的恩怨情仇娓娓道来。又似一个尽职的放映师,把形形色色的血与爱,缓慢而层次分明地映射出来。比如《麻雀》里的陈深,一个随身携带理发工具的中共潜伏者,他对行动队的上司毕忠良有着救命之恩,对伪装成演员的地下党员李小男有着兄妹之谊,对军统特工徐碧城有着暧昧情愫,对军统特工唐山海有着英雄相惜之情(海飞甚至让两者的名字暗合了“深海”这个著名的代号)……海飞将陈深塑造得有血有肉,却又冷酷无情。为了信仰他可以不认自己的儿子,可以面对妻子死于眼前而无动于衷……。再比如《捕风者》中的苏响,一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大小姐,但命运将她逐步推向了残酷的斗争。她的三任丈夫卢加南、程大栋、陈淮安先后牺牲,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孑然一身的她带着他们留给她的一张藏在怀表里的照片,一枚金戒指,和一支钢笔,以及三个只能思念的孩子:卢杨、程三思和陈东,选择继续前行。在海飞笔下,“他们”很真实地存在着,演绎属于“他们”的人生,或喜或悲,或爱或恨,或生或死……
在那样一个年代,因为信仰,他们可以抛家舍业;因为理想,他们可以牺牲生命。他们抛却生命为的是等待天亮,等待重逢,尽管他们很多最终没能活着继续等待,但是他们的信仰已如遍地开放的野花。在这里,孤岛时期的爱情,只能在记忆中深埋。我们说,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一样的,无论远古之爱、秦唐之爱、海飞笔下孤岛时期的上海之爱,以及我们此时此刻之种种爱,还有大街之爱和沙滩之爱,都延续了欢愉与疼痛。欢愉是因为情感获得了某种满足;而疼痛则是因为信仰,他们不得不把爱埋葬在某个黑夜,难以寻觅。
我只能说:小说很遥远,而爱分明就在眼前。
在一场场危机四伏、惊心动魄的谍战中,海飞有条不紊地冷静地讲述着属于那个时代的故事,似乎一切都像江水奔流一样自然,却皆是出于作者的匠心独运。小说里随处可见伏笔铺陈,当作者揭晓谜底时,你会恍然大悟道原来宰相是陈深的老婆,皮皮是陈深的儿子,原来陈曼丽丽的代号就是张生,原来原来……原来一切是那么合情合理,却又出乎意料之外。
这个集子,让我们窥见了海飞对旧上海的浓重情结,这或许和他童年时期生活在上海有关。那个早已逝去的时代,在海飞笔下得以重现,而又那样真实自然,真实得让我置身其中。例如《旗袍》中的女主人公关萍露身着漂亮的旗袍,风姿绰约,举手投足间韵味无穷——只因旗袍是那个年代上海女性最好的符号和意象。看到海飞笔下的旗袍,不禁会联想到张爱玲笔下的旗袍,瞬间我们会有一种恍惚,似乎白流苏等人的灵魂在海飞小说中又复活了,只不过她们身穿旗袍不是为了获得爱情,而是以旗袍为旗帜,义无返顾的走向她们信奉的终点。而小说最终带给我们的感觉,诚如海飞自己所说:我要如何描慕《捕风者》中的三个女人,不同的境遇不同的人生路线却有着相同的信仰,她们一个又一个坚定地倒下,像一张随风飘落的梧桐叶片,如此静美。






 猜你喜欢
猜你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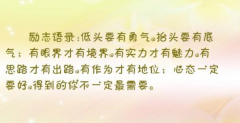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