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杀敌或被杀,我们终将获得胜利!我们将战斗!我们将死亡!但我们绝不接受妥协——阿扎尔﹒纳菲西(伊朗)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条河流,蕴藉着混沌,诱陷和重聚的能量。我们一旦将自己的根没入其中,便逃脱不了挣扎,对抗,闪避,直至最终被浸没的完局。幸好,我们还有信仰,它将我们的灵魂从冰冷的河水中捞起,穿过那些幽暗的空间和时间,飞向温暖光明的彼端。至此,我们才能真正得到救赎。海飞小说集《麻雀》中的两个荡气回肠的中篇,便都是与信仰有关的故事。
小说《麻雀》紧紧围绕谁是“麻雀”展开,海飞十分明智地选择了麻雀,谁都知道麻雀是一种平凡至被漠视的鸟类。它们随处栖息,勿用矫饰,是闹市中天生的隐者。多数的时候,它们是缄默的,只在极偶尔时被人们以隐蔽的目光注视。为了抵达信仰,革命者们将自己化作了这样一种存在。医生,宰相,麻雀,布谷,这些用平凡的代号标识己身的革命者在上海滩搅起冷冽汹涌的潮头,他们以不同的面貌在海飞笔下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中游弋:会剪发做头的特工,爱划拳的三流演员,年轻的邮递员……交错繁芜的身份背后系着不谋而合的坚定信仰:我们将战斗!我们将死亡!但我们终将获得胜利!
这就是麻雀的力量。
一系列暗杀,死亡,密谋和爱情,以及惊心动魄的暗战,在《麻雀》这个小说集里轻快地飞驰,从这一节到下一节,不断分岔,递进,繁殖,在每个细节的枝桠上开出血色灿烂的花。人时未尽,人世冗长。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交替的上海“孤岛”背景在海飞笔下犹如一瓮炽热喷薄的炉火,各色灵魂火舌般舞跃。是金子还是渣滓,是战斗还是妥协,是生存还是死亡?各种选择纷至沓来,而海飞则像是伫立炉前炼金的术士,手法娴熟,目光悠长。造就了代号为“麻雀”的革命者,光辉而绚烂的人生。
捕风,是麻雀另一种动态的存在。小而薄的翼,在腾空瞬间掀起的微弱气流,待至彼端,竟或能化为席卷一切的飓风。大革命背景下,信仰的执守与死亡本是一对孪生兄弟,是两根绳索上同一个节点。大共同体本位为基底之下的个人意愿原本就如草芥。自由的定义在国家与个人的经验之下是完全不同甚至相抵的存在。正确的指向当然只有一处。海飞的另一个收入《麻雀》中的小说《捕风者》中,主人公苏响阴差阳错踏上革命之路,在需要决断的时候,总是做出了贴近死亡却也更贴合信念的抉择:与爱情无关的重婚,将孩子全都教给梅娘抚养,冷静惩戒叛变的丈夫……这些行为与举止,都让苏呼不像一个女人。但坚定信念,决绝意志的双重环扣,是使她能在内心保持警醒纯洁的唯一屏障。
革命者的外部形象与精神内质在《捕风者》的文本中以一种反比对照的样貌出现:苏响频繁变换的身份下暗扣的玄机;梅娘粗鄙外表掩映着一颗金石质地的内心;风流娇柔的陈曼丽丽在稀薄星空下的弄堂里从容赴死……作者用这样的处理使那些细小的,动人心魄的瞬间,因为灌注了所有痛楚而显得情绪饱满。彼时,生命的真正重量才如同一颗颗细小的沙粒浮出水面,聚集成塔。
我相信这是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也相信海飞得心应手地重述上世纪四十年代繁华与萧条中的上海。在小说合集《麻雀》中,海飞在文本中采用了一种特别的温柔叙事:简单轻盈的句子,文字如柔板一般和缓。上海弄堂的天空,云朵,从瓦楞上掉落的雪雾,路灯的温暖微光,《送别》的悠长歌声……这些语词泛着江南的水汽氤氲在文本里,而速度感却渗透到叙述的情节排布和角色情绪交迭的内里。缓与急的节奏在两条线上各司其职,好似平行,实则互为因果,内有传承。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曾说:“好的小说家要像一只八面来风的狐狸。” 意思大概是说,每个细节之上都另有回声。那么,阅读海飞这部中篇《麻雀》时,或许能完成你对一只狐狸的想象。






 猜你喜欢
猜你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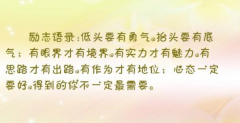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