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難,難于上青天
窮人家孩子的上學問題,何嘗不像寸步難行的蜀道一樣,生活的苦難艱辛。他很嚴肅很認真地盯着老四寫作業。
牆角裏有一隻貓,貓身融入黑暗裏,分辨不出它的樣子,僅露出藍幽幽的兩個亮光。老四一會沖貓吹口哨,一會拿着手裏的鉛筆去挑撥燈芯,猝不及防地 “砰砰”吃一記腦瓜崩兒。劉老漢的手猶如鐵錘一般硬,痛的老四滿眼淚水。老四憋着嘴,委屈地說:“燈太暗,看不清楚寫字。”王婆子停下手中的活,長長地歎口氣,滿是内疚的說,:“家裏條件差,苦了孩子呀。”劉老漢嚴肅的表情松懈下來,無奈的地說:“隻有這個條件,還是要努力讀書。沒有文化,跟我們一樣在農村苦一輩子。”劉老漢朝牆角走去,揮起手,把影響孩子學習的貓趕跑,可是他趕不跑小四的想法。小四看着家徒四壁,她不想念書,也不喜歡念書,希望像同齡的小芳一樣去廣東打工。
第二天的放學後,小芳跑來找老四,詢問是否一起出去打工。老四緊張地用手指示意一下,膽怯地說“噓噓噓,我還沒有問我爸媽,估計他們不會允許。”小芳繪聲繪色地聊着外面的燈紅酒綠,繁華熱鬧,這正是老四向往已久的生活。老四失落地望著遠方的天空,一隻離群的大雁正在往南飛,一個念頭出現在她的腦海:不如偷偷離開。
晚上,像往常一樣,飯後,父親教她寫作業。這時,父親從他的破布包裏拿出一盞新的煤油燈,淡綠色的玻璃燈瓶,中間有一根很粗的燈芯。加滿煤油,點上火,紅豔豔的火焰将燈瓶照得晶瑩透剔,房間也被照得明亮了。平時王婆子看不見納鞋底,都舍不得把燈芯挑亮,爲了她換了新油燈,不由得鼻子酸酸的。
新将房間照的明亮,灰黑的牆壁,掉漆的座椅,破舊的床鋪,瞬間将她送回到貧苦現實。她來不及感動,她心裏填滿了明天之後的美好生活,收拾起僅有的幾件衣服。王婆子看著她東挑西揀找衣服,心裏明白幾分。王婆子沒有制止她,隻是感歎起劉老漢的成年舊事,他常年勞作在地裏的辛苦,撒費苦心送她上學。她的思緒一下子被帶回那個下雪的夜晚。
1993年冬季,傍晚時分,突然下起鵝毛大雪,周圍的村莊、農田、菜地裏都被大雪覆蓋了。劉老漢在隔壁村幫老李家修葺房屋。散工回到家門前,頭發上落了一層積雪,胡須上的融化成冰渣子。進門便問:“菜地裏的白菜收了沒有?”王婆子躺在床上,有氣無力地回應他:“我還是死了算了,不中用了。快扶我起來,我要去菜地。”劉老漢沒有應她,對坐在門檻上看著雪發呆的女兒說:“老四,照顧你媽。”他扭頭就往菜地裏走去。
一邊飛快地走,一邊在心裏咬牙切齒地咒罵着可惡的天氣。冰天雪地的寒氣,都冷卻不了他對生活的殘酷無情的憤恨的怒火。一想到白菜凍壞了,賣不出價錢,一家人的生活就更加窘迫,撕心裂肺地罵的更兇。來到菜地,他看到渾身被白雪蓋住的白菜,緊鎖眉頭,呆呆地看着發愁。這些雪花猶如覆蓋在他的心上,将他整個人都冰凍着。想着往後的日子,他感覺自己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原找不到方向,無助又絕望。他用皺紋密布、滿是老繭的雙手拂去菜上的積雪,快速收割着。手漸漸地被冰凍的紅腫了,麻木了,但他已經顧不上這些。
等收完白菜,已經是夜裏十點多,夜晚的天空被雪花印得白晃晃。他勉強擡起已經直不起來的腰,望著一望無際的白茫茫,如釋重負般喘着粗氣,用口對着凍得發紫的手吹一口氣,手冒無知覺。管不了這些,他擔着白菜,一步一滑地往家門口走去,進門時,又是滿身的雪花。
災禍總不單行。那年,雪大路滑,往年進村收菜的客商不知蹤影。看着家裏成堆的白菜爛在家裏,無疑在給艱難的生活雪上加霜。
飯碗被白菜霸占的整個冬天終于熬過去,陽春三月,眼看老四開學了,她的學費還沒有着落。傍晚,劉老漢下地回家,不得不朝着當地最有錢的表弟家裏走去。高大的紅磚瓦房裏點着蠟燭,燭光支在殺豬的案板上。小四在門外遠遠地看着劉老漢,他怯怯地走進去,頭低的很低,低聲下氣地喊了一聲,還沒有張嘴借錢,臉紅的像案板上绯紅的豬肉。劉老漢多想躲在黑暗裏講借錢的事情,但是蠟燭發出的光那麽亮,刺他的眼痛,有點睜不開。父親在燭光下佝偻着背站着,低聲下氣的樣子,也刺痛了老四的眼,刺的他兩眼淚花花。
他下意識地用手擦眼睛,擦醒了陷入回憶中的自己。不知何時,自己已是滿眼淚花。她扔下手中的衣物,默默地往煤油燈走去,翻出課本,沒有左盼右顧,沒有心不在焉,沒有應付式的一通亂寫,而是一筆一劃地、認認真真地做完作業。
或許她明白了父親的良苦用心,或許她被如山的父愛感動,亦或許那麽艱苦的生活,父親都扛過來,她相信自己也能扛過來!她決定要拼盡全力努力讀書。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穷人家孩子的上学问题,何尝不像寸步难行的蜀道一样,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题记
一片空旷的旷野中,有一座低矮的茅草房,摆放着一张乌漆墨黑的四方小矮桌。桌上有一盏棕黑色的小煤油灯,灯芯斜趴在小灯盆里,探出一点头,燃烧着,发出微弱的昏黄的火光。盆底沉积着一层厚厚的黑渣滓,使得小火苗时不时地跳跃着,发出“吱吱吱”的响声。
灯光在王婆子的身上游走,映红了她的黝黑干瘦的脸庞。她坐在桌子旁的矮凳上,迷着眼睛,枯黄的双手娴熟地织毛衣。织长针发涩时,往稀疏的头发里来回刮两下。尽管常年织衣纳鞋,眼睛熬坏了,但并不影响她。她快速地松针收针,操纵自如。
老四爬在桌子上写作业,灯光很暗,他凑的很近,几乎要挨着作业本。字写得很小,隔远看,像匍匐前进的一排蚂蚁。刘老汉佝偻着背站在他后面,常年累月的辛苦劳作,已经把他的脊梁压弯。他黝黑的双眼深陷像是两个深不见底的深渊,藏满生活的苦难艰辛。他很严肃很认真地盯着老四写作业。
墙角里有一只猫,猫身融入黑暗里,分辨不出它的样子,仅露出蓝幽幽的两个亮光。老四一会冲猫吹口哨,一会拿着手里的铅笔去挑拨灯芯,猝不及防地 “砰砰”吃一记脑瓜崩儿。刘老汉的手犹如铁锤一般硬,痛的老四满眼泪水。老四憋着嘴,委屈地说:“灯太暗,看不清楚写字。”王婆子停下手中的活,长长地叹口气,满是内疚的说,:“家里条件差,苦了孩子呀。”刘老汉严肃的表情松懈下来,无奈的地说:“只有这个条件,还是要努力读书。没有文化,跟我们一样在农村苦一辈子。”刘老汉朝墙角走去,挥起手,把影响孩子学习的猫赶跑,可是他赶不跑小四的想法。小四看着家徒四壁,她不想念书,也不喜欢念书,希望像同龄的小芳一样去广东打工。
第二天的放学后,小芳跑来找老四,询问是否一起出去打工。老四紧张地用手指示意一下,胆怯地说“嘘嘘嘘,我还没有问我爸妈,估计他们不会允许。”小芳绘声绘色地聊着外面的灯红酒绿,繁华热闹,这正是老四向往已久的生活。老四失落地望著远方的天空,一只离群的大雁正在往南飞,一个念头出现在她的脑海:不如偷偷离开。
晚上,像往常一样,饭后,父亲教她写作业。这时,父亲从他的破布包里拿出一盏新的煤油灯,淡绿色的玻璃灯瓶,中间有一根很粗的灯芯。加满煤油,点上火,红艳艳的火焰将灯瓶照得晶莹透剔,房间也被照得明亮了。平时王婆子看不见纳鞋底,都舍不得把灯芯挑亮,为了她换了新油灯,不由得鼻子酸酸的。
新将房间照的明亮,灰黑的墙壁,掉漆的座椅,破旧的床铺,瞬间将她送回到贫苦现实。她来不及感动,她心里填满了明天之后的美好生活,收拾起仅有的几件衣服。王婆子看著她东挑西拣找衣服,心里明白几分。王婆子没有制止她,只是感叹起刘老汉的成年旧事,他常年劳作在地里的辛苦,撒费苦心送她上学。她的思绪一下子被带回那个下雪的夜晚。
1993年冬季,傍晚时分,突然下起鹅毛大雪,周围的村庄、农田、菜地里都被大雪覆盖了。刘老汉在隔壁村帮老李家修葺房屋。散工回到家门前,头发上落了一层积雪,胡须上的融化成冰渣子。进门便问:“菜地里的白菜收了没有?”王婆子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回应他:“我还是死了算了,不中用了。快扶我起来,我要去菜地。”刘老汉没有应她,对坐在门槛上看著雪发呆的女儿说:“老四,照顾你妈。”他扭头就往菜地里走去。
一边飞快地走,一边在心里咬牙切齿地咒骂着可恶的天气。冰天雪地的寒气,都冷却不了他对生活的残酷无情的愤恨的怒火。一想到白菜冻坏了,卖不出价钱,一家人的生活就更加窘迫,撕心裂肺地骂的更凶。来到菜地,他看到浑身被白雪盖住的白菜,紧锁眉头,呆呆地看着发愁。这些雪花犹如覆盖在他的心上,将他整个人都冰冻着。想着往后的日子,他感觉自己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原找不到方向,无助又绝望。他用皱纹密布、满是老茧的双手拂去菜上的积雪,快速收割着。手渐渐地被冰冻的红肿了,麻木了,但他已经顾不上这些。
等收完白菜,已经是夜里十点多,夜晚的天空被雪花印得白晃晃。他勉强抬起已经直不起来的腰,望著一望无际的白茫茫,如释重负般喘着粗气,用口对着冻得发紫的手吹一口气,手冒无知觉。管不了这些,他担着白菜,一步一滑地往家门口走去,进门时,又是满身的雪花。
灾祸总不单行。那年,雪大路滑,往年进村收菜的客商不知踪影。看着家里成堆的白菜烂在家里,无疑在给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
饭碗被白菜霸占的整个冬天终于熬过去,阳春三月,眼看老四开学了,她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傍晚,刘老汉下地回家,不得不朝着当地最有钱的表弟家里走去。高大的红砖瓦房里点着蜡烛,烛光支在杀猪的案板上。小四在门外远远地看着刘老汉,他怯怯地走进去,头低的很低,低声下气地喊了一声,还没有张嘴借钱,脸红的像案板上绯红的猪肉。刘老汉多想躲在黑暗里讲借钱的事情,但是蜡烛发出的光那么亮,刺他的眼痛,有点睁不开。父亲在烛光下佝偻着背站着,低声下气的样子,也刺痛了老四的眼,刺的他两眼泪花花。
他下意识地用手擦眼睛,擦醒了陷入回忆中的自己。不知何时,自己已是满眼泪花。她扔下手中的衣物,默默地往煤油灯走去,翻出课本,没有左盼右顾,没有心不在焉,没有应付式的一通乱写,而是一笔一划地、认认真真地做完作业。
或许她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或许她被如山的父爱感动,亦或许那么艰苦的生活,父亲都扛过来,她相信自己也能扛过来!她决定要拼尽全力努力读书。






 猜你喜欢
猜你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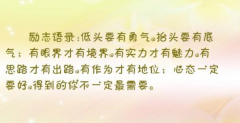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