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府的中心是一片阔大的湖面,烟波迷蒙,白鹭低徊,无数个院落隐没在山丘湖水间,它们自成一格,却都有或高或低的围墙。三年前我造访韩府时,这些院落并无围墙,那时屋宇间都是以石径曲桥相接,间或也互为映衬,构成一些特别的景致。这些楼阁散布在山水间,山水间有奇葩异卉为点缀,又有雾气氤氲,徜徉其间,虽有移步换景之妙趣,却也难免使人迷失来路或去向。(第82页)
如此大量的空间环境描写,在这部小说中比比皆是,与中国传统的绘画、诗词戏曲不无同工之妙,说起来也无特别之处。不管是从传统还是现代的意义上,环境、风景或者空间描写都是基本技法,然而,在注重人物及内在意蕴的现代小说叙事上,环境描写甚至退居到了次要位置。但庞贝的叙述却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要在空间环境方面建立起一种情境,一种氛围,给予人物和故事以特定的情态。对于他的小说来说,情态和意境、韵致和风格,可能是小说的重要美学品质,在这一意义上,《无尽藏》的古典意味是落在字里行间的。
当然,《无尽藏》的空间意识也是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作者很可能读过约瑟夫•弗兰克的《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Spatial Form in Modern Literature)》和巴赫金的《小说中的时间和时空体形式》这些论述小说叙述空间的著作,这使作者对描写的事物在空间中的“并置”尤其敏感,并倾注笔力。当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博尔赫斯的《指南针与死亡》、《小径分岔的花园》、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肯定熟读这些作品,并且已经心领神会。庞贝在徐徐展开的韩熙载的那张《夜宴图》上,演绎着精微的西方现代小说艺术,这不能不说是他功课做到家,功夫做到位。
当然,《无尽藏》的底蕴确实是古典性占据主导地位,整个故事的史料性使得这部小说的历史性和古典性结实可靠。庞贝显然在史料考证方面下了足够的功夫,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有史料可依,所述故事正史野史多有佐证。在如今大量的写历史的小说中,做到如此地步的作品,实属少见。这更不是网络穿越小说任意编造附会所能比拟。《无尽藏》的叙述如同古典工笔细密画法,也用足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词风来写南唐世风人心,江山变故,命运多舛。故而读来往事历历在目,有如亲历其境。这是印证名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也正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整个体验、感觉、心性的历史性和古典性,使得这部小说确实韵味独到。西方现代小说的意识与方法,能自由地穿行于古典场域中。今天能把中国传统性(或古典性)与西方现代小说方法结合得较好,也当推《繁花》与《无尽藏》,前者因为当代性而气象纷呈;后者则因为古典性而意蕴十足。
《无尽藏》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很显然,这是为了寻求亲临历史的逼真性效果的需要。“我”的第一人称叙述无疑有诸多的优势,第一人称使叙述,尤其是转化而来的历史叙事更具有真实性。但第一人称也有明显的局限,叙述视野受限于“我”的视野,只能在我的身份和能力的范围内。尤其是“我”如果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物角色,如何使我的自我审视准确恰当,“我”的正当性不会陷于自恋与自夸,并非能够轻易做到。文学史上有公案,据说英国小说家伊夫林·沃认为用第一人称单数来写小说是可鄙的。周熙良先生在毛姆《刀锋》译者序言中提到这则公案(参见周熙良译《刀锋》序言)。毛姆在《寻欢作乐》中,离开主题,借叙述者阿申顿之口,对第一人称写小说发表看法:“有时候,小说家觉得自己像上帝,他想告诉你关于他的作品中人物的种种方面,可有时候他又不觉得自己是上帝了,这时他就不对你讲关于他的人物的所有应当知道的事情,而是他自己所懂得的那一点;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像上帝,我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小说家们年纪越大越不愿写超出他们个人生活经验范围的事情,针对这一有限的目的,用第一人称单数来写就成了一个极为有用的方法。”(参见《寻欢作乐》) 如此,毛姆还觉得不过瘾,次年再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即以《第一人称》为名。无独有偶,多年后,诺曼·梅勒也因为在《儿子眼中的福音书》中使用第一人称而遭致人们的疑问。有记者问:“你怎么有勇气用第一人称来写耶稣?”梅勒辩解说:“我使用第一人称完全是一个实际的决定,因为我希望耶稣是书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这个人,而不是耶稣上帝之子。我总觉得他是真正强有力的分裂人格的首例,因为一方面他是一名男子,另一方面他又是上帝之子。于是我想,我还没有准备好去写上帝之子,但或许我可以写写这名男子。现在要做到这一点,你不得不具备实感性——第一人称的那种力量就能给你实感性。”(参见拉莫娜·科瓦尔《探寻孤独斗室的灵魂》,胡坤、王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第69页)
这些争论或许可以用于评析庞贝用第一人称来写林公子,那些自我的心理审视,那些观看的视角,那些亲历的真切感受,庞贝试图切近的人物心理与性格。在小说中,林公子是第一主人公,目击家庭变故,父亲忠勇可嘉,南唐御敌的第一骁将,但遭遇陷害,国主李煜竟然不辨真假,杀死父亲。正值冠礼的林公子就此与国主李煜有杀父之仇。小说一直是以复仇者的形象来塑造林公子,全部的视点都来自林公子,小说确实是写出了一个蒙受劫难,虽文弱却担当道义的古典青年形象。他有哈姆莱特的忧郁,却没有丹麦王子的迟疑,为报杀父之仇,他隐藏山林,直至南唐国破,他追杀至大宋,借宋皇之手,赐死李煜,以平父冤。这个人物写得充分饱满,内含诗意,富有文人气,古典意蕴十足。整部小说几乎就是林公子的独白,与他有较深的感情交流的人物就是飘然若仙的女道士耿先生了。他们的关系也让人捉摸不定,甚至林公子自己也把握不清。是恋母?是什么恋?耿先生的身世形象一直不清晰,固然这是作者有意为之,但过分迷朦在本来就十分诗意化的叙事中,就更难盠清。耿先生仙风道骨固然气质非凡,有一种特殊美感,其形象十分令人可敬可佩。但她来去无踪,如天外来客,又显得过于虚幻。非凡本领,沟通了武侠小说和网络文学的那种路数,可读性强,适用于青年一代读者,这种元素融入这部骨子里颇为“现代”的“纯文学”作品,是否协调?似乎还有待讨论。往好里说,是打通了雅俗共赏的界限,拓宽了当代小说表现的路数。从传统小说的方法来看,耿先生的人物形象还显得有些隔,虽然与林公子如影随形,但多数情境还是飘忽不定,小说中两个最主要的人物关系不够清晰,也未必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另外,李煜作为林公子的复仇对象,一代南唐后主,与林公子交集还显单薄。作者的历史主义态度,限制了在虚构上多做手脚的余地,如果在林公子、耿先生、李煜三人之间的关系更为集中且内在,从这里再生发出性格命运及形而上的哲思,小说当会产生更加饱满且有内在张力的意趣。当然,这都是苛求,只是我的一己之得,未必恰切。






 猜你喜欢
猜你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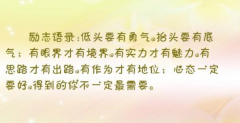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