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是一部四十万言的长篇小说,计由“天问”、“地问”、“心问”三部组成;每部下辖诸章,依次为10、8、10(章),共计28章;每章又由若干节组成,少至2节,多达10余节,数目不等。文本采用如此繁复的叙述组装格式,显然与其物色的特殊类型的“叙述人”有关。
《羊》中的“我”,名胜惠,女;出生于抗战时期的革命老区,红色后代;很遗憾,文革时含冤而死。几十年过后,她竟然又复活了,重“回”故里(梨花庄/画眉城)意图“归宗认亲”。但父(仇二狗)母(兰菊)垂危,无暇自保;同父异母的妹妹、弟弟,极度厌世;三叔老态龙钟;至于诸多的父老乡亲,各有各的的纠结;故土风物,一派凋敝……,她的“寻访“之旅,犹如一场精神漫游:由“城”及“乡”,复又返“城”。情景毫不怪诞,体贴入微,言之凿凿,均是谵妄激扬的话语。每次出动,不乏“奇遇”;为之壮行的有“风”,有“雨”,还有“残阳夕照”,“鸡犬之声相闻”。多样化的知觉、印象,栩栩如生,氤氲生烟,烘托出其隐忍而行时深情而妩媚的一面,表明着她不再是幽怨离魂的替身,复仇厉鬼的魅影,她执意要与俗世和解,为自己“正名”,于是乎,她又“追思”她之所以陷入当下狼狈不堪境地的前世今生……,文本叙事的谵妄之旅,于是乎全面启动。
而就具体情形而言,《羊》的第1、11、19章,居于各自所属之“部”的首位,含纳的是纯然的“寻访”叙事,完全有别于文本其余诸章“复式”叙事混搭倾向,或承载方式。“复式”叙事是由“奇遇”、“追思”组成,自然锁定着相应的“戏剧化”配置,拒绝了思接千载,神与物游的比兴化的诗意浸染;此类叙事装置,主要集中在(——除了上述提到的3章,以及第6、12、20章之外,总计)22章的各章首“节”。相对于用散文化的笔致记叙其过程、场面、感想的“寻访”而言,“奇遇”的叙事特性异常诡异、微妙。
首先,和父老乡亲的不期而遇,写实性倾向愈强,相应的交往愈是和“寻访”亲人的行为相接近。其次,在亲情的蛊惑下,亲人也会主动造访魂归故里的胜惠的,但却出现在“梦”中,这,岂不是对“寻访”发生的非现实性假定的实属谵妄的“寻访”行为的互文性的巧妙的颠覆?三,父亲曾犹如“托梦”似的向亡女披露心迹,说明了被他带出去的同乡“牺牲”的真相;这一幕俨然是“梦中之梦”的翻版。“追思”叙事何尝不是如此?第一人称叙事,本来就是由“当下”回顾“过去”,在“过去”的语境下又创设出另一维度的“回顾”,其情形就像鲁迅《野草》中的名句“我梦见自己在做梦”那般吊诡,毕竟“追思”在文本中乃是尾随“奇遇”而至,容易招致误解,譬如说,将之看着是常规叙事中“时—空”逆转的那类“倒叙”话语,理解为受因果律支配的“戏剧化”手段;有鉴于它被委以重任,担承了文本“主叙”的架构,“追思”的叙事本性,则不能简单地以想象的谮越、跨界、变形的动向来解释了。
不消说,介于“寻访”(谵妄性的认识假定)和“追思”( “天问”、“地问”、“心问”之“问”的创造激情)之间的“奇遇”, 无论怎样,总之始发缘构于亡灵复活的由“死”及“生”的存在论假定;海德格尔就曾认为,人是面世而在的,向“死”而“生”的,此在的这种必然律,是不能诉诸认识论的因果联系来加以诊断的;坚持生生死死之类的循环性推论,只能陷入存在二元论的认识迷雾,加剧存在本质的遮蔽。“寻访”的谵妄性,被“奇遇”的现实性所接手时,其实就蕴含了存在的解蔽的性质,以其为中介,“追思”就可以了无挂碍地超逾一切即成的谬见,直抵生命的暗夜,重建“天”、“地”、“人”、“神”共同筑居的世界。《羊》不可思议的叙事追求,于是经由“寻访”—“奇遇”—“追思”的繁复多变的“程式化”的运作,全面地潜入到“乡土中国”的历史深处,借助个体无从修复的、破碎的“成长”幻象,为那些任人宰割的“猪”、“羊”,顺从的“蚂蚁”另立新传,其“情节”是非连续性的,其指涉是中心化的,青黄杂糅,姱而不丑。
梨花庄的父老乡亲主要是在《羊》的前两部中得以展览。他们所享受的这份隆重的艺术待遇,显然是为最后一部闪亮登场的胜惠的父亲大造声势,以期突出胜惠因其父亲所纠结的爱恨情仇,整肃旷世恩怨所潜伏的悲剧性元素。此外,随着他们集体地在叙述中隐遁,玉米则成为了他们的“形象”的代理;同理,姗姗来迟的父亲也有其“形象”的代理,即张久妮,——权力对日常生活全面渗透,为之互为镜像的秘密所在。而母亲与胜惠“形象”间的对立、紧张,更是充满了结构性的张力,如同明、暗两线,牵制着文本“寻访”—“奇遇”—“追思”总体叙事的走向,何况与母亲“形象”相肖的人物也不在少数,譬如奶奶,银宝婶。鲁迅对他保姆有一句赞辞“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但她们却还不配享有类似的赞誉,因为她们已经被黑暗所压跨,承受苦难的意志严重匮乏。
无论怎样,这类奇异的人物总之是由“追思”叙事具体打造的。正因为他们是“梦中之梦”谵妄场景的过客,她们的形象化面目“息息变幻,永无定形。”毕竟文本不屑于就其个性、心理做琐细、委婉的刻镂,何况处在躁狂状态下的叙述人,不允许有娴静或雅致的定力,来抵御其内心的狂潮。






 猜你喜欢
猜你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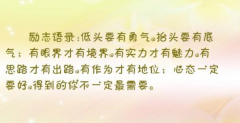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