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写完信,就交给梁思成和金岳霖看,问他们可有补充,于是我们看到了接下来由金岳霖写的一段:“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却实实在在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把他们两个搞混。”金岳霖写完,梁思成又接过信来附言道:“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板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注:梁思成因车祸脊椎受损,一直穿着协和医院为他特制的钢马甲),从我下方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这封信写在又薄又黄的劣质纸张上,不分段,字极小,没有天头地脚,连多余的半页都被裁去,为了节省纸张和邮费。这封信让远在华盛顿的费正清夫妇笑了很久,接着又心酸了很久。
梁思成曾经不无夸耀地说:“人家讲‘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但是我觉得‘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林徽因的才华是多方面的,少女时代起,她已经是颇有名气的诗人,同时翻译西方文学、创作剧本、发表小说;学了建筑以后,在设计和测绘方面也多有建树,与梁思成一起完成了许多建筑学著述。虽然穿着窄身旗袍、体弱多病,但她爬起古建筑穹顶来却根本不成障碍,金岳霖到他们家去,常常看见林徽因和梁思成爬在自家屋顶上,为野外测绘练基本功,老金当即作了一副藏头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嵌了这夫妇二人的姓氏,上句打趣梁思成,下句奉承林徽因。梁思成很高兴,林徽因却一点也不以为然,“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的,好像一个女人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只配作摆设似的!”她怎么可能是摆设?在她家客厅的著名沙龙里,任何谈笑有鸿儒的对话,她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即使重病中都躺在沙发上跟客人们大谈诗歌与哲学。曾经的沙龙客之一萧乾回忆说:“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沈从文)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是。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女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够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然而一位受男人欢迎的的女人却往往是很难与女人相处的。这话虽然有些绝对,也并非真理,但在林徽因身上确实得到了极好的验证。林徽因在北京居住期间,北京总布胡同三号的家里一群中国近代史上优秀的男性经常围坐在一起,众星捧月般地来聆听林徽因这位沙龙女主人的演讲。其独到的见解和连珠的妙语不时引来这帮男人的喝彩。美丽飘亮的外表,超凡的谈吐,征服了经常光顾客厅的这些男性,以至于他们成了这里的常客。男人们有多喜欢林徽因,女人们便也会对她有多排斥。当时文坛上大名鼎鼎的冰心俗心难耐,醋意大发,发表了《我们太太的客厅》来讥讽林徽因,林徽因也毫不示弱,从山西考察归来的她,将一瓶上好的山西老陈醋送给了冰心。由此留下了中国文坛上的一段趣话。
可惜,林徽因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个“兴奋型的人”,情绪喜怒不定,像朵带电的云,“只凭一时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做事”,所以,她留下的作品并不多。述而不作的她,其聪明智慧,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传说,流传在那些见识过其聪慧的文化名人们的口头笔端。而战争、疾病、政治运动、贫穷而琐细的家庭生活又剥夺了她大量的创作精力,所以,抛开她那些著名的“绯闻”,在学术层面上,人们通常只知道她是国徽的设计者、北京古建筑的积极保护者,而忽略了她内心更加丰沛的才华。被肺病折磨半生,她终于在1955年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离开了这个带给她太多幻想,也让她承受了太多痛苦的世界。比梁思成幸运的是,她躲过了后来席卷全国的“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没有经受惨无人道的人祸带来伤害。丈夫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碑上移来她生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她的知己金岳霖为她组成治丧委员会,悉心料理后事。人生得此,夫复何求?






 猜你喜欢
猜你喜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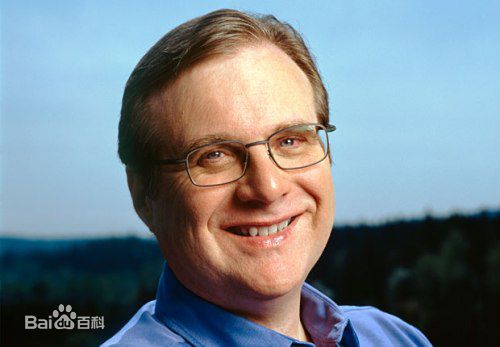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